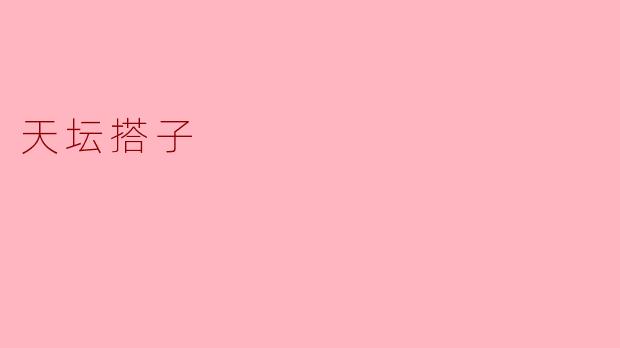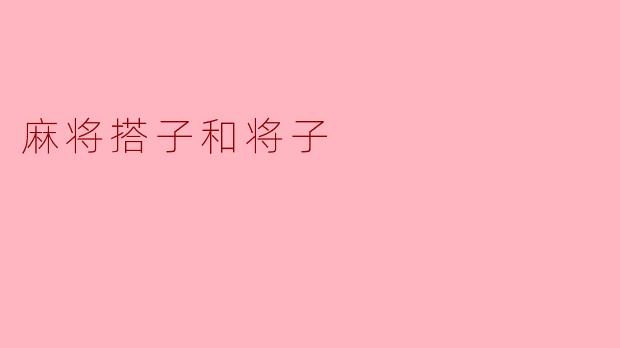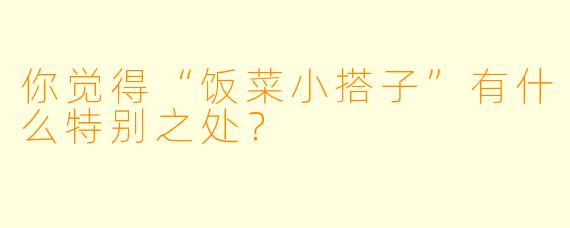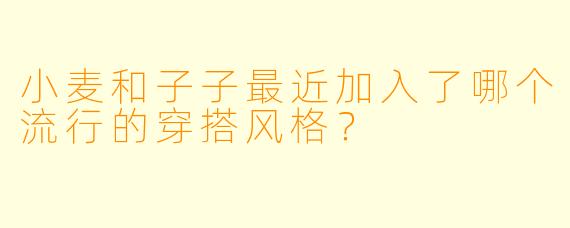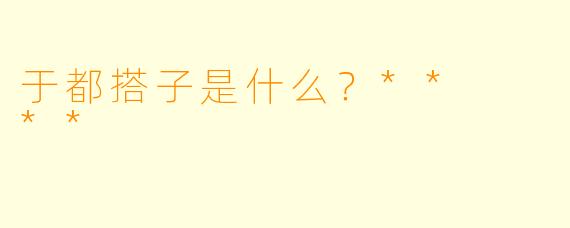什么是“模型搭子”?

“模型搭子”是网络流行语,指在搭建或训练AI模型(如机器学习、深度学习)时,互相协作、分享资源或交流经验的伙伴。类似“学习搭子”,但专注于模型开发,比如一起调参、跑实验、讨论技术问题等,能提高效率并减少“单打独斗”的孤独感。
模型搭子禄丰搭子:滇中古道上的商贸传奇与文化纽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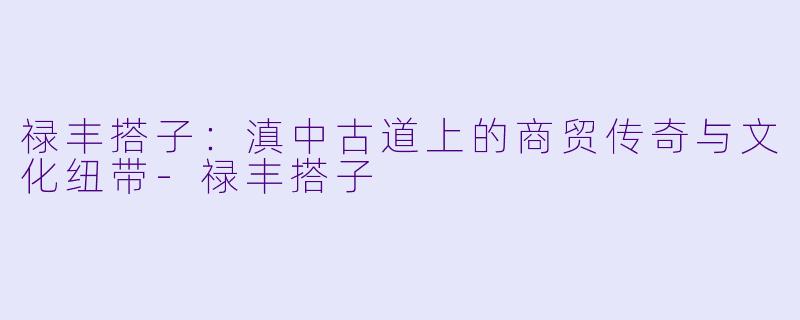
在云南禄丰的千年历史长卷中,"禄丰搭子"并非简单的交易工具,而是滇中古道商贸智慧的缩影。这种以竹篾编织而成的背具,曾是马帮时代最可靠的运输伙伴,其独特的双层结构既能承重百斤盐茶货物,又可分隔易碎物品,堪称高原上的"移动货仓"。
禄丰搭子《会东酒搭子:川南小城的烟火气与江湖味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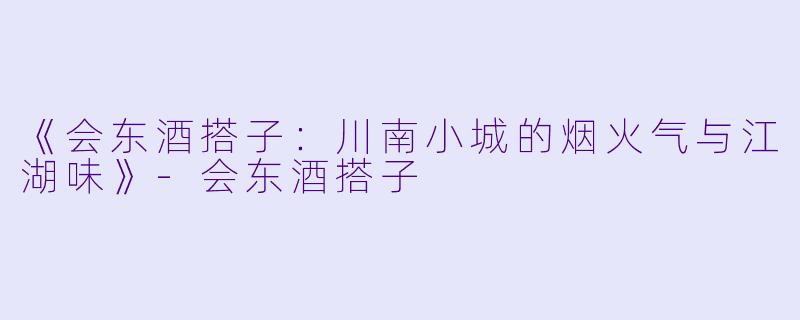
在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县,街头巷尾藏着一种独特的市井文化——"酒搭子"。它不是精致的酒局,也不是孤独的独酌,而是三五熟人围坐,一瓶本地苞谷酒、几碟花生米或烧烤,就能撑起半晚的热闹。
会东酒搭子《晨练搭子:当早起不再孤单,健康路上有你有我》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凉意,公园的跑道上已陆续出现三三两两的身影。他们或快走、或慢跑,偶尔相视一笑,默契地调整步伐——这就是“晨练搭子”,一群因共同目标而结伴的陌生人,用陪伴让早起和坚持变得更容易。
晨练搭子《爱尔兰搭子:跨越山海的文化纽带与温暖情谊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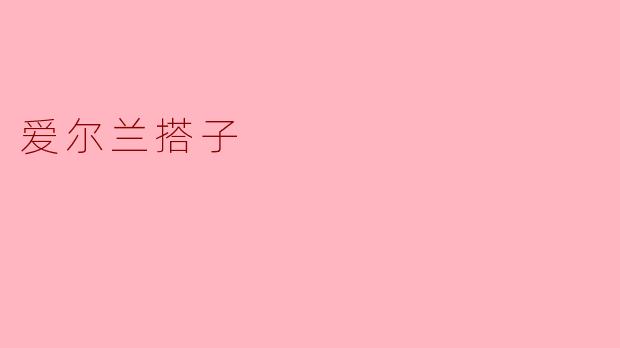
在全球化浪潮中,“搭子”文化悄然兴起,而“爱尔兰搭子”则以其独特的文化包容性和温暖底色成为跨地域情谊的缩影。无论是结伴探索翡翠绿岛的自然奇观,还是隔着时差分享一杯虚拟的健力士黑啤,这种轻量而真挚的联结,正重新定义当代人的社交距离。
爱尔兰搭子《鞍山跨年搭子:烟火人间里的温暖相遇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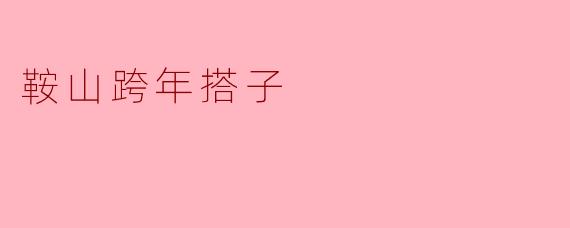
岁末的鞍山,寒风裹挟着节庆的热闹,街头巷尾的彩灯与商场橱窗的“新年快乐”交相辉映。在这座钢铁之城,一群自称“跨年搭子”的年轻人正用独特的方式告别旧岁——他们或许是素未谋面的网友,或是偶然相识的同城伙伴,因一句“一起跨年吗?”而聚在一起,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里,用陪伴焐热了时光。
鞍山跨年搭子《小圈搭子:当代年轻人的轻社交与情感代餐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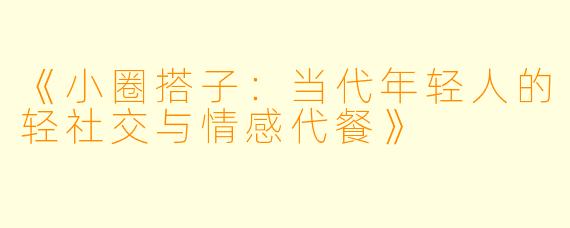
在“搭子文化”盛行的当下,“小圈搭子”正成为年轻人社交图谱中的新坐标。不同于泛泛之交的饭搭子、游戏搭子,小圈搭子特指在特定兴趣或需求中结成的小范围、高默契伙伴——可能是深夜聊小众音乐的三人群组,周末一起做手工的线下工作坊成员,或是坚持打卡同一健身课的“镜友”。这种关系剥离了传统友谊的情感负担,以“精准陪伴”为核心:无需频繁维护,却能在特定领域提供即时响应。比如,二次元同好群里的“谷圈搭子”互相代购周边,摄影小圈中的“互勉搭子”约定互拍创作。它的魅力在于“去中心化”——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圈子扮演不同角色,既享受归属感,又保有个人边界。心理学家指出,小圈搭子的流行折射出年轻人对“低功耗社交”的需求:在原子化生活中,用模块化关系填补碎片化情感需求。但争议也随之而来——当人际关系被拆解成功能化零件,我们是否正在用“搭子”的便利性,逃避更深层的联结?或许答案藏在小圈搭子的潜规则里:那些因共同热爱而自然滋生的信任,那些在“只聊烘焙不谈私事”的表象下,悄然生长的默契。它未必是亲密关系的平替,而是当代社交生态中一种诚实的妥协——先找到同类,再决定是否走向更远。
小圈搭子小说搭子的照片:虚构世界中的真实连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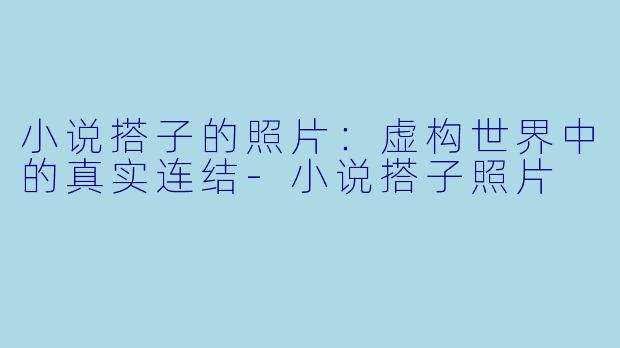
通过这样的方式,小说搭子的照片在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,让我们看到了读者对故事的深切共鸣,也让小说的魅力得以延续与传播。无论是纸本小说还是电子书,这份热爱都在每一张照片中发光。
小说搭子照片想参加周末的羽毛球搭子球局,但水平一般,会不会拖后腿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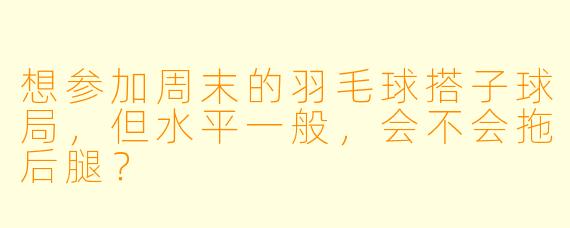
完全不用担心!搭子球局就是为了让不同水平的人一起娱乐锻炼,通常会有分组调整,新手老手都能玩得开心。提前说明自己的水平,组织者会帮忙安排合适的队友~
搭子球局聊天搭子和游戏搭子有什么区别?** **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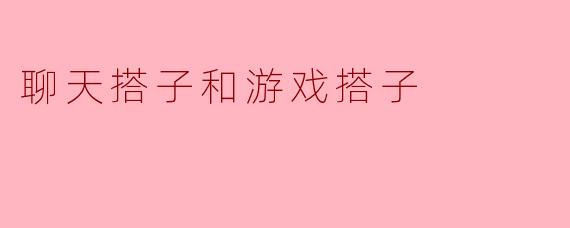
聊天搭子主要是指可以频繁进行交流和分享心情的伙伴,而游戏搭子则是一起玩游戏、互相配合的队友,它们的侧重点不同,一个注重情感交流,一个注重娱乐互动。**
聊天搭子和游戏搭子### 梅园区的“搭子”文化:友谊与生活的新方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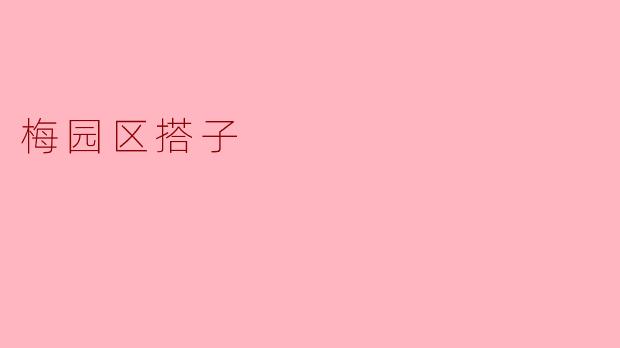
在梅园区,许多居民通过“搭子”进行健身、购物、旅游等活动,彼此之间在互动中增进了了解和信任。无论是一起晨跑,还是组团去看电影,搭子的存在让生活变得更加多彩。同时,这也成为打破孤独、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。
梅园区搭子《盐田饭搭子:打工人的“舌尖社交”与城市温情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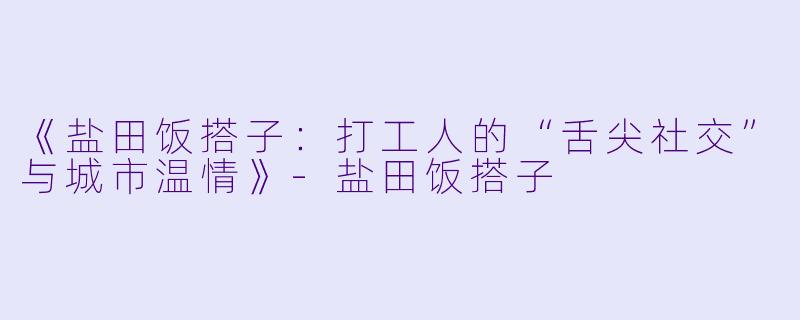
在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码头附近,有一群特殊的“饭搭子”——他们可能是叉车司机、仓库管理员,或是报关行的文员。每天午休时分,这些素不相识的打工人们会默契地凑成一桌,拼单点菜、分享盒饭,用一餐饭的时间卸下疲惫,聊家长里短、谈工资油价,甚至互相介绍工作机会。这种自发形成的“盐田饭搭子”现象,成了工业区里最鲜活的市井图景。
盐田饭搭子《以画为媒,寻楚辞中的山水知音——我的“楚辞画画搭子”之旅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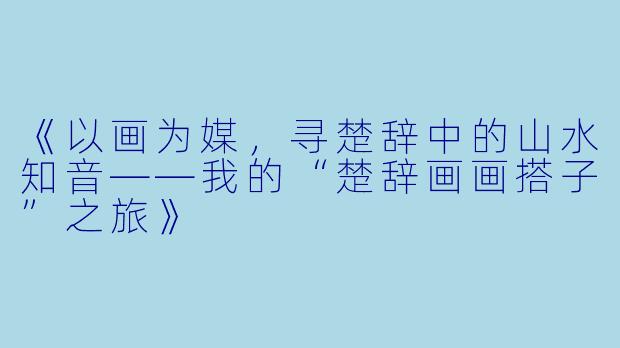
在喧嚣的日常里,我总想为灵魂寻一处静谧的归处。偶然翻开《楚辞》,那些瑰丽的香草、缥缈的云霓、悲怆的吟咏,突然在心底撞出一幅画来。于是,“楚辞画画搭子”这个念头悄然生根——若能找到同好,共执笔墨,将《湘君》的烟波、《山鬼》的幽林、《离骚》的佩兰一一绘成丹青,该是何等风雅?起初只是独自尝试。用淡墨勾出《九歌》中“袅袅兮秋风”的意境,却总觉得少了些灵韵。直到在线上画社遇见几位“楚辞迷”,有人擅工笔,能细描《少司命》荷衣蕙带的飘逸;有人爱写意,以泼墨渲染《天问》的混沌苍茫。我们约定每周共绘一章,画毕互评,偶尔争执“东皇太一该戴怎样的冠冕”,或笑谈“屈原若见现代水彩会不会皱眉”。最难忘的是合作《招魂》长卷。我负责“层台累榭”的楼阁,她专攻“蝮蛇蓁蓁”的密林,另一人题写“魂兮归来”的篆字。当三部分拼合时,竟有种跨越时空的默契——原来《楚辞》的魂,从未离去,只是借我们的笔,在纸上又活了一次。如今,“楚辞画画搭子”已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仪式。我们不仅复刻文字里的画面,更在色彩与留白间,读懂了两千年前那个“纫秋兰以为佩”的孤独诗人。或许艺术最动人的部分,正是这般:以古典为舟,以知己为桨,共渡人间寂寞的江河。
楚辞画画搭子![[搭子]Logo](https://www.wdazi.cn/logo.pn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