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途有伴,便是团圆——记我的“回家搭子”过年
腊月的风裹着车站广播里断续的乡音,吹得人心里发慌。行李箱轮子碾过斑驳地砖的咕噜声、人群裹挟着泡面与汗水气息的嘈杂,以及电子屏上不断跳动的车次信息——每年此时,这场名为“春运”的迁徙,总是中国大地最沉重也最温情的注脚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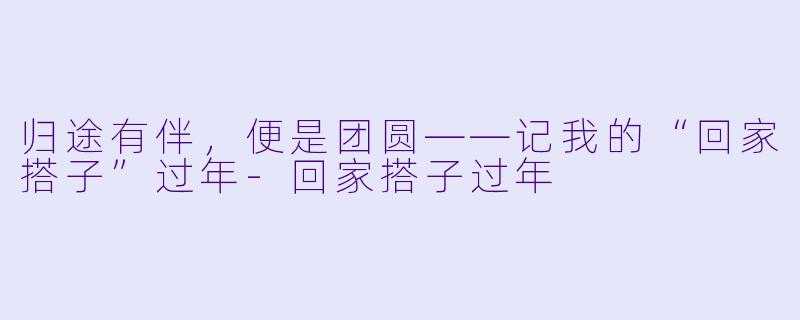
而今年,我的归途多了一个人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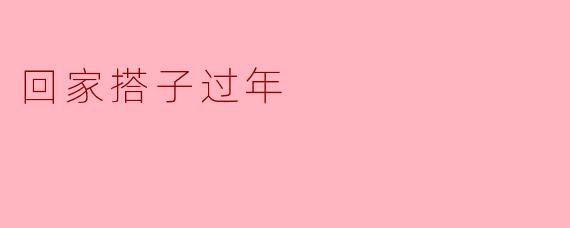
她是我的“回家搭子”,小悠。我们同在一座远离故乡的城市打拼,在一次同乡会上相识,发现两家竟只隔了两个县城。于是,“一起买票,路上做个伴”的提议自然成形。原本漫长到令人畏惧的、需要独自扛过十几个小时的旅程,忽然变得值得期待起来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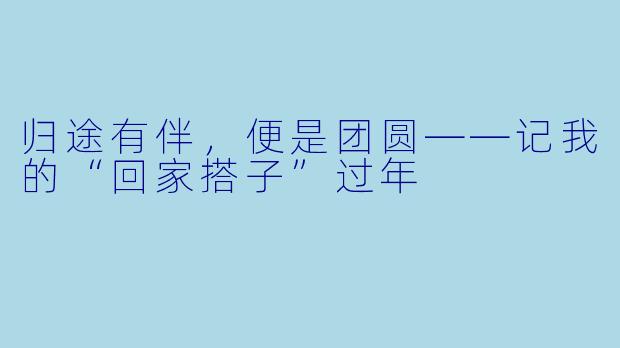
抢票时,我们屏息凝神地守在各自的屏幕前,仿佛进行一场精密协作的战役;成功后,在微信里发出的那一连串狂喜的感叹号和表情包,瞬间冲淡了年关工作的所有疲惫。我们开始分享行李清单,她提醒我给她妈妈带的膏药别忘了,我拜托她帮我多带些本地买不到的年糕。回家的行囊,因此塞进了双份的牵挂。
真正的旅程始于熙攘的候车室。我们像两个连体婴,一人看行李,一人去买热水;一人排队等检票,一人不断确认站台信息。穿过人潮的那一刻,我不再是孤身一人,彼此的一句“跟上!”,就是最安心的力量。
火车轰隆,载着满厢的乡愁南行。窗外的风景从城市的棱角分明渐变为田野的萧索开阔。我们分享同一副耳机,看同一部下载好的电影,分食同一盒洗好的草莓。更多的是聊天,聊这一年的漂泊与收获,聊家里催婚的爸妈和淘气渐长的侄辈,聊记忆里故乡年的味道——她家必备的腊肉,我家独有的糖环。那些对家人难以细说的委屈,在对着同龄人的倾诉中,得到了温柔的共鸣。漫长的时光,被切割成一块块轻松愉快的碎片。
深夜,车厢灯光暗下,她靠在我肩头浅眠,我望着窗外偶尔划过的零星灯火,心里一片宁静。独自回家时,那灯火是别人的温暖,而此刻,肩头的重量让我感到,我不是在奔赴团圆,我正在创造一种新的、路上的团圆。
列车终于到站。在出站口那更为汹涌的人潮中,我们看到了各自翘首以盼的家人。没有夸张的拥抱与呼喊,只有妈妈们迅速接过行李的双手和爸爸们略带腼腆的笑。
“走了啊!年后再见!” “好,快回去吧,代我问叔叔阿姨好!”
我们匆匆道别,像两滴水,迅速汇入各自家庭温暖的河流。甚至没有好好说声谢谢。
但我知道,这份情谊已然不同。我们曾是陌路,却因同一片土地的召唤而结伴,互相托付了一段最焦急也最幸福的旅程。我们分享了奔赴团圆的焦虑与甜蜜,用陪伴稀释了乡愁的浓度。
“回家搭子”,这不只是一个出于实用的组合,它是现代社会中,一种微小而确定的温暖。是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,在庞大的春运系统里,为自己找到的一个盟友,一份依靠,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共渡。
团圆,是终点站那顿热腾腾的年夜饭。而幸福,有时也是归途上,有人陪你一起,走过这段长长的路。
![[搭子]Logo](https://www.wdazi.cn/logo.png)